◎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
创业资讯门户网站

全球连锁酒店格林豪泰的老板徐曙光曾这样描述他对孩子家庭教育的感受:“本来,这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每天下午主要处理美国公司的事务,晚上处理格林豪泰在中国的事务。有时候懒的时候,今天做的事情做不完,只能拖到第二天.直到有一天,我看了孩子发给我的一篇日记,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女儿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周末终于可以睡懒觉了,可以像爸爸一样睡到11点。”徐曙光读到这里时觉得不对劲。虽然他一点也没有因为努力工作到半夜而懈怠,但是他发现他的孩子不会看到这些。他女儿只看到他爸爸早上11点才起床,他也要像他爸爸一样。女儿甚至开始觉得11点起床就好了,哪怕是很晚才睡。然而,徐曙光仍然意识到他在睡觉方面给女儿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在和孩子的各种前前后后的争执中,类似的事情让徐曙光为难了很久,他也意识到家庭教育是一件比他做生意更难的事情。为此,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做父亲,不许失败的创业》。
另一位父亲蔡博士也在其家庭教育专著中说,“父亲”是我一生的事业和人生理想,孩子是我最大的荣耀。蔡晓认为,父亲教育的缺失会使孩子人格缺钙,父亲对孩子的成长和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没有坏爸爸,只有懒爸爸。父亲不能再扮演“有而无”的角色。
因此,蔡在《我的事业是父亲》一书中谆谆开导他人,无论多忙,都可以做一个好父亲。他从实用性出发,通过《100个龙芯细节》强调了父亲在育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弥补了家庭教育领域父亲教育内容的不足。让很多爸爸深以为然,这是一本让大家重新正视自己在家庭做父亲不许失败的创业教育中重要作用的好书。
估计谁也想不到蔡晓夜的教育细节,就算想到了,也很难坚持下去:比如每晚陪孩子;比如总是让孩子走在前面,坐在前排,比如故意给他们赢得辩论赛的机会,比如哪怕是最大的错误也不惩罚他们,比如自己写三字经教他们,比如给孩子的玩具是球台,比如带着孩子去旅游,要设计他们的路线,比如带着孩子玩存折游戏……为了让爸爸出一番事业,蔡小小后来也做到了。
“高知家庭”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学会接受“你能做到的,孩子不一定能做到”
有二宝的余爸爸是上海某高校的青年教师。他所在的小区离学校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所以大部分居民都是同一所学校的教职工。在这样一个充斥着“高知家庭”的住宅区,出现了一个可笑的现象3354。每天晚上7点,各家各户窗外飘来各种乐器,“吹啊,弹啊,唱啊,什么都有”。直到9点左右,出现了不同分贝的“吼声”,有的来自愤怒的老母亲,有的来自恨铁不成钢的老父亲。宇爸爸笑着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很同情别人家的孩子,但其实自己的宝宝也在面对“鸡血妈妈”的“怒吼”。
“孩子的教育培养是很多家庭的重中之重,但对于知识分子家庭来说,似乎更为迫切。”爸爸于坦言。
陈骁和他的妻子都毕业于Xi交通大学,是另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父母”。女儿一岁的时候,他们去参加一个大学同学聚会,提到对孩子的期望,他们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不会比我们差吧?”今年夫妻俩想尽办法,花了1000多万在上海市中心换了一套学区房,为三年后的“幼幼小战”做准备。
“一个出生在‘高知家庭’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往往背负着父母和爷爷奶奶的高期望,但这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无形压力。”在心理学上,这种压力被称为“背景压力”。——越是来自“高知家庭”、拥有优质资源的孩子,或者提前“起步”,越容易承受背景压力,可能会驱使孩子厌学、自卑、叛逆。
心理咨询师徐博表示,父母有“期待孩子成功”的心态很正常,但“高知父母”会把自己或遇到的更好的人作为孩子成长的参照系,他们会经常向孩子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我们为你创造了更好的基础和条件。你应该也必须更有出息,至少不能比我们差。换句话说,他们潜意识里拒绝接受“我能做到的,孩子不一定能做到”的假设。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孩子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考上名校。否则就是失败的人生。”徐波说。
在上海一位高中心理学老师看来,“知识分子家长”大多是学生时代的尖子生,是应试教育的赢家。尖子生有一个典型的心态:对成功的渴望很高,但背后其实是对失败的恐惧。对他们来说,保护自己的自尊,保护自己不被失败伤害,比成功更重要。在心理学上,如果“成就动机”过高,只是暗示了一种自我怀疑。
接受错误和失败,接受孩子的错误和失败,可能是“高知父母”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80后”的父母:天生焦虑,也传递焦虑;崇尚教育,却容易“用力过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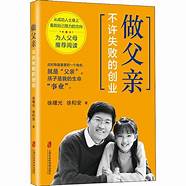
经常有“80后”自嘲为“经历过很多‘第一’的一代”: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年轻的一代,他们见证了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是独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皇帝”、“小公主”;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扩招,第一次坐上了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幸运列车,却赶上了“毕业不保证分配”的就业难题。可以说,“80后”是从焦虑中一路走来的。现在作为父母,学历普遍较高,对教育的期望值和育儿的焦虑值也较高。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80后”之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焦虑父母”和“鸡血父母”,与其代际特征有关,也与其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
“80后的父母通常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一代经历了时代的剧变。有的人因为有知识改变了命运,有的人因为没有知识错过了人生机遇,所以特别看中了教育。”董卿的父母毕业于复旦大学,父亲是报社总编辑,母亲是大学物理系教授。她曾提到,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娃,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坚持,她考上了名牌大学。所以父亲相信“吃了苦才能做好人”,他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复旦大学长三角80后世界社会变迁调查》(——)也支持这一观点。数据显示,上海80后群体教育的代际传递尤为明显:父母受教育程度对80后子女受教育程度有正向影响,父亲每提高一个学历,子女受教育程度平均增加0.42岁;母亲每提高一年教育水平,其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将增加0.38年。
现在,“80后”把父母的厚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再一次传递给下一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孩子和父母总是处于不同的时代。我们早期为他们准备的东西有用吗?毕竟没有人能完全预测未来。
那么,在“知性父母”的光环或阴影下,孩子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成长?徐博的建议是“做自己”,但他强调,前提是父母要给孩子做自己的空间,而不是让孩子只是“父母的孩子”。
编辑:朱英杰
编辑:范立平
余爸爸的80后父母徐青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