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
创业资讯门户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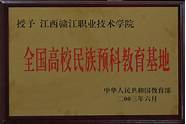
然而,直到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仍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孕育和成长。真正能接触到互联网的人还是很少的。大多数普通人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甚至没听说过。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
它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与全球化的浪潮密不可分。
20世纪末的1999年,在大洋彼岸的互联网发源地美国,由于资本的疯狂介入和推动,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互联网泡沫狂潮开始出现,但人们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泡沫的到来。很快这股狂热逐渐蔓延到了中国大地。狂潮虽有泡沫,却在不经意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2000年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特殊的一年。如果说在这之前,互联网只是在少数人中间流行,那么在这一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时间,各种术语和词汇,如万维网、WBE、域名、网站、BBS、论坛等。在懂的人和不懂的人之间激烈争论;一个又一个样本,受到海外资本的青睐,诱惑着一批热情的年轻人。今年很多年轻人都很兴奋,很激动,跃跃欲试。有人认为,眼下只要想办法办个网站,马上就能拿到钱。虽然一切似乎都有些过度,但在中国,至少很少有人感觉到任何泡沫。这种趋势加速了中国人进入互联网的进程,加深了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扩大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影响力,当然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对互联网的重视。很快,在中央高层的直接介入下,人民网、人民网等5家全国重点新闻网站相继诞生。以Dongfang.com、Qianlong.com为代表的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也在各省市迅速崛起。新浪、搜狐、网易等商业网站加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今年年初,我还在经济部。像往常一样,我每天早上准时走进我在5号楼的办公室。习惯性的打开电脑,打开当天的报纸,高速浏览。如果没有紧急情况,打开“情况汇编”、“大参考”、“小参考”、“理论参考”等各种资料和文件,用最短的时间,尽快浏览一遍,找出需要时间推敲的东西放在一边,以便有空时仔细阅读。传阅和领导指示,需要根据轻重缓急加快处理。然后是细节和样本的审核,还有同事投稿的审核,帮助年轻编辑修改稿件;自己写稿,思考制定报道计划,处理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等等。
我不记得那是五月初的哪一天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志发给我打电话。老袁长期在内蒙古工作,从内蒙古调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个子不高,有些壮,低调善良。他不分管经济部,我跟他打交道也不多。见面时,我们总是彬彬有礼,毕恭毕敬。我觉得自己是个谦虚的人。后来调任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直至退休。根据编委会的工作安排,他也有分工,即协助邵华泽主席分管人事工作。当时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们经济部是谁管的,其他人管什么。我不知道老袁有这样的分工,所以我不知道他和我在一起做什么,有什么事。
这是一次坦率的谈话。他明确告诉我,编委会让我负责网络版。说实话,我有点惊讶,但还是很耐心地听他说。虽然他是在和我协商,征求意见,但我觉得这是一次严肃正式的谈话,不是随便说说。他多次肯定我之前的工作,很多都是表扬,说是俱乐部领导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表达了对我未来的极大期待。甚至还有一些暗示性的内容。谈话中,我说了很多为我着想的话,对我有点触动。他显然是想让我接受报社的这个安排。
谈话持续了一些时间,中间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下一步,中央主管领导有意将海外版与网络版合并,取消纸质报纸,全力办好网络版。这个网络版不再是原来的网络版,它将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领域,关注,社会领袖们都看好你。
关于取消海外版,据说是这位中央领导出国时听了华侨的反映后想出的主意。这显然是一种先进的理念。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纸媒将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消失,中国将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这个想法在当时中央领导的直接追问下并没有实现(我也真的不想实现)。据说海外版的同事已经给中央主要领导写过信,说明了它存在的背景、成就和意义,得到了主要领导的认可。后来,他们不再打算合并。这是后话。我上任的那天,还没有明确的决定,所以很自然的,主编徐中天通知海外版主编丁正海参加我的入职会。
当然感谢俱乐部领导的信任和关心。我没有当面拒绝,也没有明确同意,只是说会认真考虑编委会的工作安排。这是一次普通的对话,但对我来说,却非同寻常。它关系到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记得早些时候,有一次主编徐中天在路上遇到我,说王庚南极力推荐你去《市场报》。你会去吗?我说,不行。当场拒绝。《市场新闻》的主编王庚南退休了,他再三要我接任。专门给我打电话,说我能重振市场报,对我寄予厚望。我不知道他的自信从何而来。但是,我没有答应。可能我知道我不会去市场报,所以我只是在路上遇到的时候顺便知道我的态度。对我来说,当官,做出一番事业是我最大的追求,其他副局、局级都是其次。说实话,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在我心里还是有点吸引力的,我觉得自己可能更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早在1996年,国内为数不多的网站之一——中国经济信息网就诞生了。因为它,我成为了中国最早的网民之一。那天,我经济部的同事董来问我,你想上网吗?她说,国家信息中心建立了中国经济信息网,这很好。如果她想上网,可以帮我向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刘鹤申请一个号。我答应了!这是最好的事情。我希望她尽力而为。
快帮我申请。当时上网,必备的条件,一是有电脑,当时,我已有台486;二是电话专线,因为只能通过电话拨号上网,这个不成问题。其他需要有个“猫”(调制解调器),音响之类。没几天,小董在清华同方的爱人来我家,很快帮我解决了问题。
不用说,我立刻体会到了互联网的神奇。虽然网上内容还不是很多,网站数量有限,关键在于但凡有链接的地方,你就能点进去,从而进入另外一个天地。这是传统媒体无法想象的。和纸质媒体完全不同。空间巨大,凭想象力、创造力,可以自由驰骋。这种一眼看不到底的体验,是美妙的,从未有过的,会深深地吸引你。当时恰逢台湾的领导人选举,我在这里看到了双方选票的实时变化。
后来,新浪、搜狐、中华等网站,以及人民日报网络版等逐一诞生,网上信息内容愈来愈多了。我差不多也成了一个网迷。
在报社大院里,有些信息很快会不胫而走。在大报总编室工作的老朋友曹焕荣来到我办公室,他说听说编委会让你去网络版,你去吗?我说我在考虑。他说,去吧,还考虑什么?他劝我的理由很简单:你看看,你在经济部该得的奖全得了,该有的荣誉也全有了,还图什么?不如到新的领域再开创一番新事业。确实,当时包括中国新闻奖的各类奖项差不多全得过,还有号称新闻界最高成就奖的范长江新闻奖,我是第三届获奖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也有了。老曹当时是总编室副主任,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劝我,老朋友的这个说辞,显然是有些说服力的。他一定程度敲动了我热衷于干事业的心。
没想到,很快许中田总编辑又找上门来,当然,也是希望我去网络版。老许说的不多,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日报编委会也高度重视。希望你开创出马克思主义网络新闻新实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网路新闻新理论来。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担子,我顿时感到了肩头的沉重。看来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二,反复
但我还是有点难以决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经济部正做的顺风顺水,而且渐入佳境。二十多年,上,熟悉各项方针政策,和国家部委关系良好,适应宏观环境;下,了解基层情况,懂得民间疾苦。经济问题,兴趣浓厚,尤其对“三农”,付出真情。
自跨入新闻事业这一门槛始,从最早一度的“农业学大寨”,到农村改革开放第一缕春风吹起;从“农村包产到组、到户”的探索,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成型;从民间集市变迁,到大市场的建立;从省际间“生猪大战”,到全国一盘棋的流通体制改革;从乡镇企业的萌芽、发展,到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从改革开放农村起步,到全面走向城市;从计划到市场……一点一滴,一步一步,伴随着思考和努力,凝聚了自己差不多全部的心血。采访、写稿;编稿、审稿;白班、夜班;策划、选题;社论、评论员、短评、编后、按语;做版面,带队伍……虽周而复始,却从不重复;始终伴随着时代的脚步,沉浮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品尝着酸甜苦辣,体会着置身潮头的快乐。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特别奖,范长江新闻奖,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及一箱子的各种荣誉证书,无一不和辛勤汗水紧密相连。我不太介意荣誉,但无形中产生某种激励,成为对过往难以割舍的因素。90年代,我还被报社确定为所谓“中南海记者”,参加了党和国家及领导人一系列重大活动的报道,虽辛苦,但充实。
由于我对经济问题的熟悉,一度时期,许中田总编辑总是把各部门准备上版的经济方面拿不准的稿件批到我这里,“请加正同志阅”,让我“把关”。退休后,曾任市场报总编辑的刘学渊一次就非常不解的问我,当时市场报的稿件,许总为什么批到你那里阅?通常是副总编辑审阅的。我告诉他当时的背景。
上下左右人际关系,也是导致自己难弃难舍的重要原因。经济部风气正,是报社有名的,它应该源自于老一辈的传统。就以我负责的农村报道这块来说,我经历的老领导有李克林、季音、姚立文等,他们差不多都是“三八式”,也就是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走进人民新闻队伍的,他们身上具有一种天生可贵的品格。国家兴亡,人民幸福,是他们的追求。季音同志曾是著名的“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姚立文长期做新闻工作,一度曾在刘少奇主席身边工作。特别是在全报社得到尊敬的李克林“李老太”,为人正派,有口皆碑。她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自然,无形之中也会弥漫成整体的风气。部门里,大家有正义感,坚持原则,相互之间又不失宽容理解。老总编辑范敬宜曾和我说过:来人民日报这么多年,分管经济部,你们部门几个领导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说过任何别人的坏话。我当时想,这有什么特别吗?大家都一心为工作,很正常啊。其实,这并不容易。在部门,我和大家相处很好,上下关系融洽。特别和年轻人,相互尊重而又信任,非常愉快。说真的,真要离开,还真有点舍不得。事后听说,知道我要去网络版后,有人找过社领导,希望我能留在经济部。
由于这种种原因,为了避免当面尴尬,同时也是我以往一贯习惯,不喜欢面见领导,有事公文来去。我给邵华泽社长写了一页纸。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经过再三思考,觉得自己还是在经济部工作更合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些患得患失?
很快,秘书电话来了,说社长找你。我知道找我干什么。社领导都在三楼,我办公室在二楼,几节台阶而已。敲开门,老邵(当时更多这样称乎)一脸严肃坐在办公桌后边,见我进来,挪坐到沙发上。我坐在对面椅子上。他拿着我的那张纸,摆了摆,一脸的不高兴,说社领导下决心好不容易做了这么个安排,你现在说不去就不去,怎么办!话语和表情明显带有愠怒,看上去有些生气。以前我没有见过他像今天这样。
我一下子感到有些愧疚。老邵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那年(1989年6月)他刚来人民日报没几天,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时刻,总体上大家说话还是比较谨慎。我最后一个发言,我一直认为,只要你心怀坦荡,就应该直话直说。记得我说了三点,首先是不同意当时有人对人民日报编辑记者队伍政治上的否定,这和前面的人发言有所不同,唱了下反调。同时,就特殊时刻的新闻报道,我提了自己的不同想法和看法,提了建议。这一点感觉他是听进去的,甚至当即表示,我建议的某类报道已经开始布置了。第三点具体说了什么,忘记了。总之,我没有说一些所谓跟大流的话。
不久中央在济南召开已停了多年的中央农村(业)工作会议,老邵作为报社总编辑参加。会议住地在省政府招待所,傍晚,他打电话让我到他房间,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准备一篇社论?我说是的,这是惯例。他说那你起草一下吧,我让家里准备版面。简单聊了几句,饭后,我便开了夜车。第二天一早把手写的社论稿交给他。他当即看了起来,稍稍改了些字句,即通过了,说让会务组打印出来送审吧。会议一结束,社论和会议消息就在在人民日报一版发表。
此后,类似这样的经历有多次,包括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都是我起草社论。他对社论、评论非常重视,任社长后,也常常亲自修改和把关。1992年,我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人民日报社论《千万不可忽视农业》,就是他修改定稿的,标题也是他最终确定的。年终报新闻奖时,由于我一贯的对评奖不是很上心,就那么随便一报,结果评上一等奖,公布时只有作者,没有编者,这使我一直内疚在心。邵社长是编辑。
创办人民日报网络版,邵华泽社长当然是最重要的决策人和拍板者。后来他对这一段工作多有回忆。现在,中央高度重视媒体向网络化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选中我,当然是一种信任。
在他办公室,我们谈话时间不长,没有再多的犹豫,我说,我服从安排,匆匆离开了。
退休后,碰到一个朋友,跟我说,看到老邵了,聊天时还特别提起了你。不久,另一个同事也这么说了,说见老邵了,他谈起了你。我突然觉得,是不是也该见一见老邵?上班的时候,领导不叫,绝对不见面。有急事,纸上来往。非不得已,绝不上门。现在退了,是不是得适当改改?下最大决心,在老邵原秘书刘新的安排下,终于登门拜访一次,时间不长,聊得高兴。显然,让我去人民网这个安排,是他得意之作之一。临别,特地赠我“大道至简”四字墨宝一幅。
再后来,据说两位友人拜访老邵,谈起我时,说当时有两个岗位,之所以让我去人民网,是觉得我有些创新精神。
谢谢老邵的信任。正当我虽然下了决心,但还没有做好转折准备的时候,6月2日一早,出现许中田总编辑要求立即就位的那一幕。无法再有任何犹豫了。
发布于:江苏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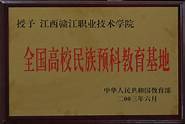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